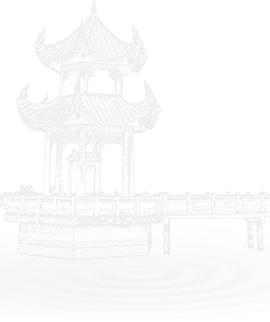大学的意义与经典阅读

大学是怎样诞生的呢?大学这个词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是指教师与学生自发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自发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谈经论道催生欧洲中世纪大学,意大利的波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莫不如此。英国红衣主教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说:“我对大学的看法如下:它是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如果大学的目的是为了科学和哲学发现,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学应该拥有学生;如果大学的目的是进行宗教训练,我不明白它为什么会成为文学和科学的殿堂。”从中我们得知:纽曼心目中的大学不是科研之地,而是教学的场地,培养人才的机构,也是保存文化和科学的殿堂。从现代大学的角度看来,此话有些偏颇。纽曼是针对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功利主义倾向而提出的主张,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智,大学的真正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要实现大学的理想,教师率先垂范,与学生和谐相处,教育以人文主义为旗帜,还要学生阅读经典,通过阅读来修身。到20世纪,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Robert M.Hutchins,1899---1977)秉承纽曼的自由教育思想,对当时盛行美国的实用主义提出批评,反对大学细分专业,强调学生的心智训练,引进名著学习与阅读。赫钦斯认为现代大学只有发展通识教育或共同教育才符合大学之道,藉此来沟通不同系科、不同专业的人,从而建立大学所有师生的共同文化语言。通识教育的内容必须是属于“永恒学习”的范畴,不仅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的特殊问题,而是人类之为人类永远需要探讨的永恒内容和永恒问题。这就是他所谓探讨“共同人性”(common human nature)以及“本族群的属性”(the attributes of the race), 这种永恒性的研究,其精华首先体现在西方文明自古以来的历代经典著作。因此,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内容就是要让大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以前,不分系科、专业全都应该首先研究“西方经典”或所谓“伟大著作”(Great Books).1947年,赫钦斯亲自担任刚成立的名著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在赫钦斯领导下,美国20世纪40年代末,面向成人的名著讨论活动席卷全国。当时约有1500万人参加了讨论,其中又一次在芝加哥交响乐厅讨论柏拉图的《论辩篇》吸引了3000人。之后芝加哥大学有一个本科生必读的书目(54本)。迄今为止,美国的中学大学大多有给学生的必读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今天的港澳台大学也有自己阅读书目。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有规定的阅读书目,如吴宓先生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系主任,提出外文系办学的原则:“培养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学,足以胜任愉快;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他本人为学生亲拟书单,其意图“为学生成为德才兼备之人必读一些好书(“To make the students read certain fundamental good books which should be read by every good and intelligent man and woman.”)。
近年来我国国民的阅读状况堪忧。 2014年4月20日公布的第12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56本,与2013年相比减少了0.21本,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58.1%,较2013年的50.1上升了8.0个百分点。而韩国人均年阅读量11本,法国人20本,日本人40本。据新华社资料,我国全国书店销售的书籍中,80%是各种各样的教材资料。(2014年4月25日《光明日报》)可见,我们国民阅读量亟需提高,大学应该率先垂范。
我们大学在激发学生阅读的自觉性之外,是否需要一份不分专业、系科学生的必读书目?如果需要,该怎样产生?将来有这样一个书单之后,有怎样的方法或措施让学子们爱读这些书,并读更多的好书。愿我们共同思考。